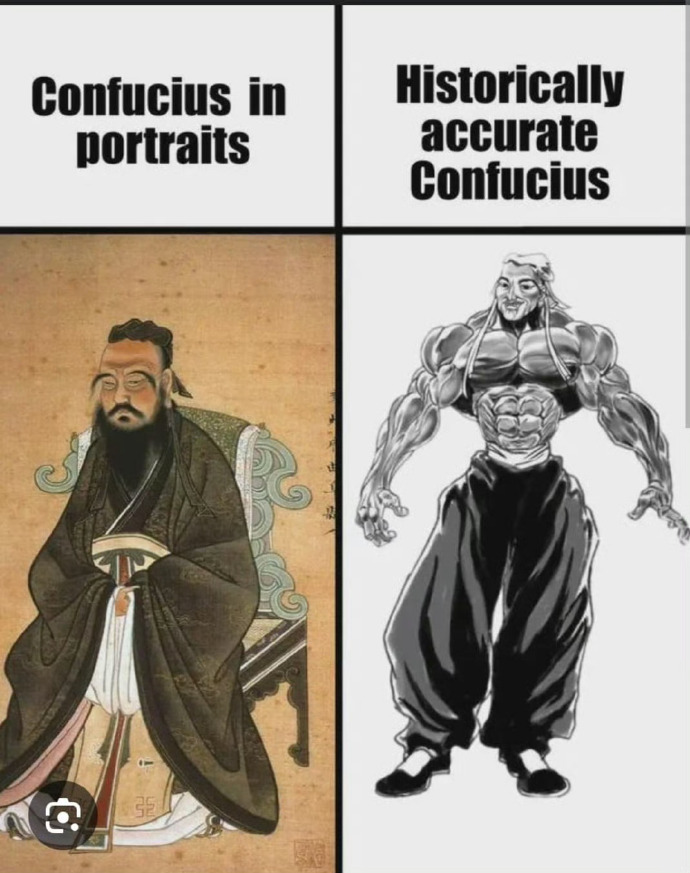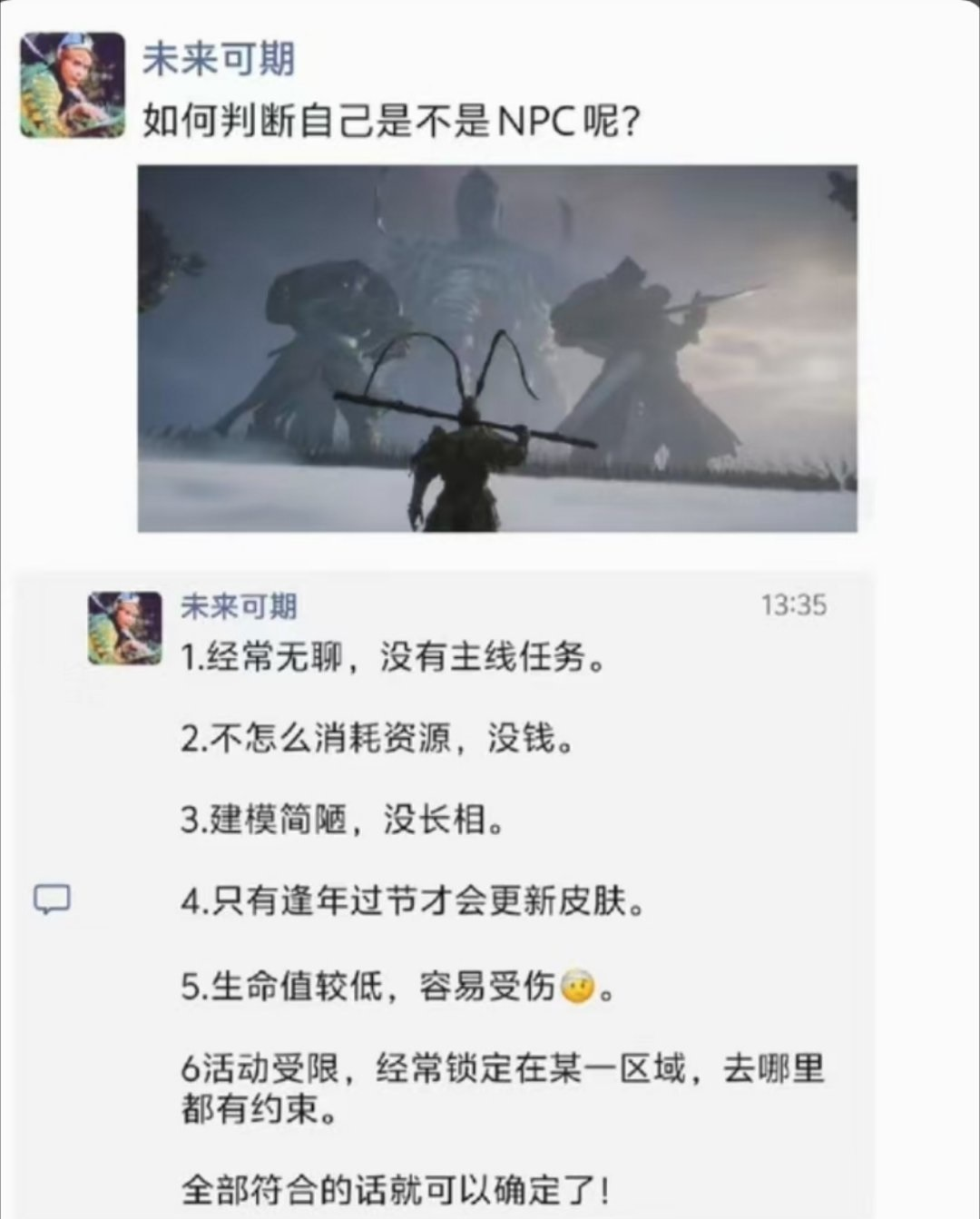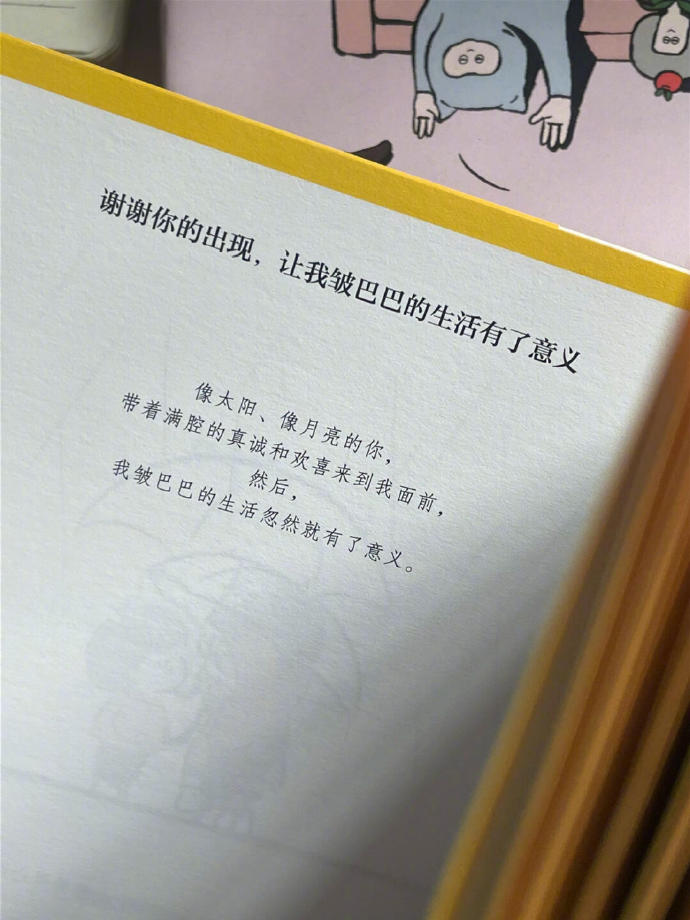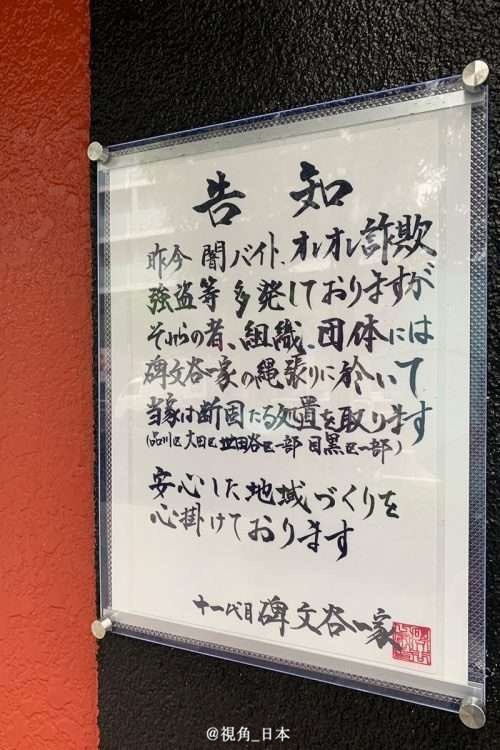六六社恭喜老李成功脱险!在六六君看来以后大家不要总说隔壁老王了,隔壁还有老李呢!这技术还真不是老王能拥有的。看来“小镇做题家”也得工具齐全才能成功啊。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老李的独门绝技吧!“小镇做题家”技术哪家强,隔壁老李是最强
老李的传说在江湖中早有流传。模仿者也如同过江之鲫,然而老李历来就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存在,下面我们着重向大家介绍几位模仿者。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小镇做题家。从小到大我喜欢读书,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被老师保护得很好。由于中考是全市前三得以离开小城进入本省的名校。又得益于这所名校在高三上期就保送清华。除了体育会考要考篮球苦练了一阵,我几乎没遇到过挫折。
我并不熬夜,我把每天的每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像高效运作的机器,驰骋向我的目标。但那时我并没意识到,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根本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在填志愿时,我的家人都在几百公里以外。我几乎是就看着专业列表望文生义就选了一个实用文科。
学会放弃是我在清华学到的第一课,因为第一年我就得了一种消耗性的自身免疫病。这个疾病延绵至今,成为此后我生命的主旋律。
我并没有一开始就放弃。我们的时代被 “意志战胜病魔” 的叙事包裹。我也不例外。
我错将疾病以为是一场战斗,终将分出胜负。我搜集这个疾病的一切机理和知识,我给自己打气,竭力把它驱逐出我的生活,至少在表面上。我甚至顶着爆炸的心率跑下了必修的 1500 米,只为了成绩单上不出现体疗课的 60 分。
是现实教我做人,让我逐渐发现 “我不能”。如我无法骑车登上某栋教学楼前的大上坡。如果顽强骑上去我会喘一节课。
如某天我去看病,回程下了公交过天桥时,在暴晒的烈日下我大汗淋漓,筋疲力尽,一边走一边发现腿在剧烈地抖。我几乎是拖着自己走到最近的快餐店买了饭买了水,吃了药,然后缓缓走回学校。
那时我意识到,这还只是个开始,甚至根本不是一场战斗。于是我果断学会了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集体活动在晚上,拒绝。小组作业要熬夜赶工,拒绝。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不理解和失望 —— 第一次以疾病原因拒绝时,会收获 “抱抱”,“好好休息” 的宽慰,而几次后,如果不是很好的朋友,就会收获冷漠甚至排斥。而这些不理解和失望更加重了我的抑郁。
我从一些圈子退场。
曾有一位老师跟我说,保重身体,来日方长。这八个字我可能会铭记一生。我曾和另一位老师聊天,她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人生就是不断失去的过程。想到未来不断的失去:健康将流逝,亲友将流逝,你以为牢牢握在手心的一切都将流逝 —— 我反而渐渐释然了。
我不能,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是一个事实。接受 “我不能” 这三个字,是早晚要到来的一个时刻。
唯一的慰藉来自知识。
大学期间,清华的选课开放度使我顺利晃荡着:必修的专业课以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人文学院和法学院晃荡。在德国交换期间,我也在这两个系晃荡。直到大三下期我从德国回来,身边人已经在准备保研或考托福,我才意识到,我无忧无虑的晃荡生涯就要结束了。
我要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了。就在下飞机的那天晚上,我突然就睡不着觉了。很快,我时而暴躁,时而低落。我去回龙观医院检查,诊断为重度焦虑和抑郁症。
那时我对人类学和法哲学感兴趣。在获得推免资格后,我完全没考虑风险地分别报了清华哲学系和北大的人类学系。前者没进面试,后者进了面试。
我借了一本人类学理论书,临阵磨枪了一周就去面试,结果毫无意外地败下阵来。我才意识到,在各个院系晃悠并不能让我转专业深造,我的毕业证上将会是一个毫无关系的专业学位。
保研失败,我就准备出国。我报了三次 GRE,两次托福,一次雅思,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崩溃只去考了一次托福。这样,我彻底放弃了去美国和英国读研。
到寒假时,我匆匆填写了一些还在招生的欧洲学校。当北欧一所大学给我发了全奖 offer 时,我稍微犹豫了下就奔赴了。录取我的专业叫电影与视听美学,而那时,我在豆瓣标记的电影 “看过” 不超过 200 部。
这个自我放逐的选择收获了一些不解,还有一些同情。甚至在出发前的暑假,我都在自我怀疑:如果我坚持一下,不顾一切考了 GRE,是不是就会有更好的去处?但是,这个 “更好” 究竟是何种意义的更好呢?
到北欧的第一个学期,因为气候、食物和住宿问题,我因为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两次,成绩单惨不忍睹,三门课分别得了 C、D、E。北欧漫长、阴冷、多雨的冬天让我每天都了无生趣。我时而不吃饭,时而暴饮暴食,很快我的胃开始报警。
真正给我这样一边晃荡一边焦虑不堪的迷惘期标出转折点的是费里尼的电影《大路》。那时我已经上完了所有硕士所有课,但扪心自问,我连专业课要求看的电影都没怎么看过,大部分时间我还在宗教学系和哲学系晃荡。
晃荡归晃荡,我对哲学的掠取只是蜻蜓点水,并没有产出。于是,我突然发现,我再次面临着要给自己找一条出路的可怕问题。我再次陷入焦虑和抑郁,抓耳挠腮,毫无头绪。由于已经没课要上,我龟缩在我的小房间里自闭。
我已经不记得我为何会点开《大路》这部电影。当赞巴诺颓然倒在海滩上,那曲悠扬的、哀而不伤的《大路》想起时,我嚎啕大哭。
之后,我又点开了《卡比利亚之夜》。再之后,我又点开了伯格曼…… 我开始了一段疯狂看电影的岁月。我躺在小床上,从天明看到天黑。北欧的冬天三点多就天黑了。
电影陪我度过漫漫长夜。
在我看到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的《利维坦》里那个把 GoPro 相机漂在海面上拍出的海鸟捕食浮游生物的镜头时,我真真切切地喘不过气来。我才意识到,“朝菌不知晦朔” 是什么意思,“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又是什么意思。
在那之前,我从清华大学 “欧陆思想联萌” 的公众号上读过几篇德勒兹的文章节选。《利维坦》给我的体验不就是德勒兹所说的生成 – 动物吗?电影和哲学,这两件我最爱的事,他们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于是,我确定了硕士论文的题目,在图书馆坐了半年,从零开始读德勒兹的哲学书。为了一些基本术语去请教哲学系的学长。有时,从早到晚,我只能读两三页。
平安夜那天晚上,图书馆下午就没人了。我不断地跺脚以唤醒声控灯。晚上十点多,我步行回家的路上,平时繁华的马路万籁俱寂,只有圣诞夜的装饰闪着光,圣诞老人的鹿金灿灿的,我仿佛感到那颗抑郁了许久的心又在跳跃。
我常常想,如果我的人生没有因为疾病偏转到这寒冷的北欧,那世界的边缘,或者如果健健康康的我有精力在大学便涉足了这个领域,也许它会因为放置于我面前的无数光彩夺目的选择而显得暗淡,而非点亮我的生命。
当然这么说好像有自我安慰的味道,但我如此感激这场相遇,感激生命还给了我这个惊喜。
还有一些在我生命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将我引向了哲学。M 是我在图书馆认识的。晚上十点,只有我和他,他在大声唱歌。我去**。然后就聊上了。他以前晃悠,**,29 岁开始学哲学。说话状态能看出在躁狂发作期,颠三倒四,思维跳跃极快。
他说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思绪像在整个宇宙驰骋。到快 12 点时我走了,他在那里彻夜思考。
E 是我的前任。他在离大学毕业只差半年时从政治学系退学。然后开始晃悠。他想搞一套把宗教、科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的哲学(施莱尔马赫一定要批判死他)。最后发表出来时无人问津。
他会对我的见解给予孩子般的惊异,会罔顾我不会丹麦语的事实让我去应聘拉斯・冯・提尔的团队。
他不懂中文坐几十个小时火车转大巴然后搭车到道教圣地天台山 “取经”,当然收获的只是道教**给他回复的微信 “哈哈” 表情。他 29 岁时,回到大学改学哲学。
S 是我的朋友。高中毕业后晃悠,**,23 岁开始学哲学。阶段性躺尸不起。阶段性躁狂阅读写作,寒假时他一次性把所有考试推到八月躺尸酗酒。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抱着一瓶啤酒问我,我们是不是一起上法语课?
我问,你本科毕业论文是啥?他说柏格森。我:!!!那你是 Deleuzian 吗?他大笑,从书包里拿出一本《千高原》。
于是到第二年,我的论文以 A 完成。我也终于下定决心去哲学系。我申请了欧陆一所学校的哲学系硕士。被告知,由于我的哲学背景不足,需要从本科开始读起。
那就读吧。
在一碗面条合人民币 100 多元的北欧,我每个月的花费不足 6000 元。我用那两年从奖学金里攒下的钱交了学费。我的同学来自各种我知道和不知道具体在哪的国家:喀麦隆,格鲁吉亚……
他们中有护士来学习照护的伦理学,有法学博士来补哲学背景,有从业多年的心理咨询师希望开创一种现象学为基础的咨询方法,有人类学家…… 我是其中人生经历最平淡乏味的一个。
我唯一特殊的地方,可能就是我和哲学的联结是由一个个不可思议的相遇产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疾病,生理的和精神的。
我仍然记得意外读到德勒兹在二十五六岁时就开始受到肺病困扰,读到他将手术称为 “器官的一次懦弱挑衅”,读到他说 “它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状态…… 它是如何改变这一切,也包括我的研究。” 而那年我正是二十五岁。
在他酣畅淋漓地表达无器官的身体时,他正经历器官 stratified 之痛,宁不痛杀?很难表达我读到这件事那一刻的心情。哭笑不得。
在那席卷一切的不确定性里,竟然好像精确地埋藏着欣慰和喜悦。我到底是怎么碰上这位精神导师,我已不能解释。大概只能说,能够拥有这样的相遇,上苍待我不薄。
而我后来的研究题目,也多与身体经验和身体美学相关。在生病后,才体会到什么是 “心悸”,什么是 “胸闷”,什么是 “气短” 而非 “气促”,以及疼痛的部位究竟是哪里,抽痛、刺痛、酸痛、坠痛,胀痛。那些抽象的词语完全能准确对应。
经验,唯有经验。痛觉让我感知到我的身体,进而感知他人同为血肉之躯的痛,速度渐渐放缓,力的涌现却更为清晰。无器官的身体,也许不是嗑了药后感官增强的身体,而是在确实的疼痛中痉挛的身体。正常的呼吸是非人的,而培根的画,卡夫卡的小说,则是 “一切困难都能击倒我”。
去年的一天中午,在北医三院做完检查等着取药时,想到下午协和的号是两点,只觉得疲惫到极点,无法动弹,而孤立无援,几乎想破罐破摔,几乎要崩溃大哭。然而举目都是病弱,又如何能打扰他们。
到不得不出发时,我强行命令自己站起来往外走,一边走一边拨通了一个心理援助热线。好笑的是,这个援助热线始终没有接通,但转接的音乐极其美妙,高亢而激越,圣洁而坚实。
让我一下想到在德国海德堡的最后一个上午,在俾斯麦广场下公交时听到有人拉《查尔达斯》,想到乌尔姆大教堂里突然奏响的管风琴宗教乐,想起那年圣诞节前和前任在老城散步听到的《帝国进行曲》,这些隐存的旋律乱七八糟地从远远的地方飘过来,乱七八糟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条逃逸线。
从北医三院到西土城地铁站,听了一路,慢慢平静下来了。与我而言,这就是哲学和电影的救赎。这就是最好的救赎。我已不期待更多。
现在的我,正在完成哲学硕士学位。在闲暇时,我写写影评,在豆瓣上写写抑郁症的哲学阐释,希望用哲学帮助到受抑郁之苦的人。我希望继续读博以成为一名以哲学为路径的电影学者。
但同时我也计划好了未来:如果身体不允许或现实不支持,就回到家乡小城找份糊口的工作养活自己即可。
从生病开始,生活强迫我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面貌。我曾经被一种目的论裹挟着。我期待人生按照学士 – 硕士 – 博士的节奏紧锣密鼓地前进,直到拿下博士学位,我才能够停下。那时我将享受鲜花和掌声。
后来我才懂得,人永远只能活在当下。拥有当下,才拥有未来。时间,是我的朋友。我早早地和成功学告别,同龄人焦虑的事于我而言十分遥远。我知道无论如何,我可以退回到家乡十八线小城,靠我的技能过活。
这是我的生活。
在很多年里,我的体重都稳定在 50kg。后来,因为免疫抑制剂和抗抑郁药双管齐下,我爆肥 30 多斤。我已经不记得从前的自己长什么样子。但我感到我正处于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我对依然活着这件事充满渴望和感激,对遇到了哲学和电影还发现了他们的奇妙结合这件事更是充满狂喜和热爱。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苏格拉底的那句话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活”,而有过审视的人生足矣。
来源:幕味儿 微信号:movie1958